這一篇決定分成四篇來寫,因為是四個問題,每一個問題都值得花上不少篇幅來談談Geertz的人生觀點,透過他最新一本譯書《後事實追尋》中第一章 “城鎮” 中的第一節,來以一種詮釋的觀點來看 Geertz 一輩子最關心的問題,也因為這一節實在是太重要,許多複雜的問題意識化為濃厚文字語塊中讓他人不易理解,透過一種詮釋的方式或許能找到正在看文章的你,與我,共同親近的經驗來了解這剛辭世不久的詮釋人類學大師的想法。
接下來這一篇是節錄Geertz《後事實追尋》第一章第一節談的東西,其實Geetz似乎迫不急待的想把他一生對於何謂人類學? 何謂研究? 何謂觀點? 做了一個最精華的整理,簡簡單單的例子與心得,卻也道盡了許多研究者一輩子感到不解的問題。
為了讓看這篇的人能夠享受Geertz深厚素養的文筆,我選擇將這一小節全文摘錄進來貼在下面,後面再談心得:
假想在大約四個十年間,你不時捲入兩個外地城鎮(一個在東南亞的一條馬路轉彎處,另一個是在北非邊城與出入口),你想要說點兒這兩個城鎮的事情有何改變。你可以對比過去與現在、之前與之後,描述過去的生活曾經如何,而至今又是如何。你可以寫篇紀敘,寫個故事說明一件事如何演變成另一件事,然後又變成了其他的事:「接著……然後……。」你可以創造指標,描述趨勢:個人主義更、宗教信仰較不虔誠、財富增加、道德敗壞。你可以寫個回憶錄,透過現在的眼光回顧過去,努力重新體驗。你可以最舉出不同階段—傳統、現代、後現代;封建主義、殖民主義、獨立—並假定這些階段通往一個共通的目標:國家角色萎縮、理性官僚鐵籠。你可以描述制度的變遷:家庭、市場、政府、學校。你甚至可以建立一個模型,構想一個過程,提出一套理論。你也可以畫圖。
問題是,改變遠比你初步印像的更多、更為支離破碎了。兩個城鎮當然變了,許多方面是表面的不同,有些許地方則是根本的不同了。但是,同樣的,人類學家也不一樣了。人類學家工作的學科不同,這門學科的知識背景不同,而這門學科的道德基礎也不同了。這兩個城鎮所在的國家、這兩個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也不同了。同樣的,大部分的人覺得什麼是生活的想法改變了。這改變比赫拉克里特斯想的更繁雜、更糟糕。無論是細微直接或是宏大抽當,當所有事情都改變了—研究對象改變了,研究對象週遭也改變了,研究者變了,研究者的周遭也改變了,以及同時包含兩者的那更寬廣的世界也變了—似乎找不到洽當的立足點來研究,是什麼改變了,以及如何改變的。
只是,赫拉克里特斯的意象事實上有所謬誤,或著說造成某種程度的誤導。時間,這種部分是個人、部分是職業、部分是政治、部分是哲學(不論其所指為何)的時間,兩是像大河在匯聚眾支流後,持續朝著某個終極目的流去,比如流向大海或是大瀑布等,而更像是或大或小的溪流,曲行彎流並不時交錯,短暫匯集併流後旋即分開。時間也不像是或長或短的循環或週期,彼此堆疊成複雜波形,需藉由調和分析器拆解出基本波形。這般時間並不是人們面對單一歷史、單一傳紀,反而更像是騷動的多重歷史、繽紛的多人傳記。這其中的確有個規律存在,但是這規律如同疾風暴雨或是街道市集般,也就是說,沒有一點韻律。
因此我們有必要接受漩渦、流竄以及不定的連貫性;就像雲聚雲散一樣。並沒有一普遍的故事可敘說,也沒有一個綜觀全局的圖像在那裡。或著說,即使有,不管是在那刻或將來,也沒有人可以像布里斯在滑鐵盧戰役那樣漫遊到故事圖像中間,有立場可以去構築他們。我們唯一可以建構出來的(假如我們持續記錄並且還能活下來)是在事情發生之後,諸事休戚相連的後見之明,也就是說,在事實之後,我們所拼湊出的模式。
但是,若有人試圖「理解」這些從我們熟知的世界中所發生的隨機劇情蒐集而得的各種材料,這一過程究竟會發生什麼,僅僅只是此道出我們的觀察,就會帶來一連串值得憂心的問題。客觀性會因此成了什麼樣? 是什麼可以證實我們的確是看對了呢? 科學此時又跑去哪裡了呢? 然後,或許人類就是以這種方式理解(如果是分散式、從下而上的大腦模型是對的,人的意識也是這樣來理解)生活而已。知識與幻覺相似之處,就在於兩者皆從已發生的事件中張皇模索,拼湊出事件如何連屬的說辭,這些說辭出自己知的觀念以及方便取用的文化工具。但是就像所有的工具一樣有特定的用途,這意昧著文化工具並不中立,在拿來使用之前早已附載了特定的價值觀。若要追求客觀、正確與科學,我們不能假裝它能擺脫加諸在它們身上的各種努力,而這些努力不是造成了它們就是毀了它們。
要我述說我的城鎮、我的專業、我的世界以及我自己有何改變,情節描述、測量、憶舊、結構性演進、圖形等並不適用;雖然這些(和模式或理論一樣)各有其功用,可以用來設定框架與界定問題。我們所需要的是去展示特定事件與特別場合(比如這邊的會面、那邊的發展),如何繁複的事實及多元的解釋編織在一起,而能有助於理解事情經過如何發生,以及將如何變化。就如有人說過(我想是諾斯洛普、佛來(Northrop Frye)),神話描述的不只是曾經發生過的事,也是正在發生的事。科學,尤其是社會科學,也適用這句話,只是科學的描述要求事實的基礎與更穩固的思考,而且有時期許達到公正客觀之境。
Geertz 這段感想,其實真的把他一輩子做研究的心得、方式、反省,用很簡單千餘字落在這裡,字字都是經過他斟酌再三而下筆(就我覺得,是的。),如果他老人家還在世,問他這篇到底在談些什,我想Geertz會再更簡單的問。‧
一.我們何以得知我們所欲了解(研究)的對象是真的?
二.又如何見我所見(如何我看見的就真的是那樣)
三.用的方法是什麼?
四.最後以上說的是對的嗎?
這四個小問題,分別一個個來說說什麼意思
一、我們何以得知我們所欲了解(研究)的對象是真的?
光是這一題就足以耗上大半功夫來談談,但這裡簡單的詮釋Geertz的想法。他認為研究對象一直在 “變”,不論研究一個國家? 還是一個民族、一個社區、部落,甚至是一個人,都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,因為研究對象不斷的在 “變”,今天研究一個部落好了,假設想研究他們朋友間送禮的關係與意義(光這一點就殺了不少人類學家的精力去研究),因為身處環境下的人,不可能真空存在於地球某個角落,當我們研究他們一年中某一天為何要送某樣東西、給某個人,要怎麼去做適當的 “研究” ,難就難在人與人的關係隨時在變動,特別又是這部落也很可能與外界互動,人與人間的默契、共識也會隨著改變,哪怕改變的再小,這研究的 “目的” ,似乎就離最初研究的假設大有不同。
當然,也可以說:我就研究某十年內的關係就好了,總要切塊來看,對吧(況且十年的研究已經夠久了),但 對 Geertz 來說,他研究印尼、摩洛哥、峇哩島等地,深深覺得不是幾年的問題,而是我們受現代思維影響太大,若以為研究任何東西,只要用不同的方法、取徑,似乎都有一種直指一項真實所在,超越事情表像背後的深層、邏輯形式,Geertz說,我們不應該被眼前的事物給弄混了,而要試圖比較多種不同的面像,去找出背後可能共同的一種 「共向性」(借點現象學的論點是說,指的人的行為總有一種所謂 “意像性”,似乎冥冥之中有些共通的做事決策法則),Geertz 為解釋這種可能的共向性,在他《地方知識》論文選裡頭比較了四個地區不同法律與道德關係,試圖去補捉不同地區人民、不同文化風俗與法律道德,其背後可能的「邏輯結構」,Geertz是這麼認為,是有可能種過一種詮釋的觀點來找到。
但這不免會被人批評為掉入了結構功能論的困境中,也就是設想任何事背後都有其在現象裡佔據某一位置、功能,所以Geertz上面一段話他說「像大河在匯聚眾支流後,持續朝著某個終極目的流去」,也就是前段我提的,世間任何事情背後都有一種共向性的可能,但Geertz提了「赫拉克里特斯的意象事實」這例子,就是在反省自己,思考我們這樣子假設任何事情背後,是不是有一種共向性的發展呢? 他仍不願放棄做為研究就是要解謎的 “信念”,所以他說「雖有規律」,但沒有「韻律」。
借用卡漫文化裡對世界的一種想像,機動戰士鋼彈裡的世界觀中,認為居住在地球之外的人類,他們稱之為「New Type」(新人類)能擺脫地心引力的影響,不論是感官能力、想像、與意志,都能有機會脫離地心引力的影響,擺脫舊世界(指地球)的框架超越人類極限,甚至想像能帶給全人類更好的幸福與未來,似乎也隱隱約約的暗指人類發展有一種「意向性」的可能,即是地心引力給予人的束縛。若沒有地心引力,或是我們現今生活在引力更小的星球,還會有牛頓發現論述了地心引力嗎? 我們還會覺得人在天上飛是種奇想嗎? 就一定不會有箂特兄弟發明飛機,或許他們會想 “也許我們該註地殼裡面鑽看看有沒有新的玩意 “。 如果要找個安身立命的切入觀點,也許我們透過這文化場域所謂 “新人類” 的想像,我們或許還能為自己研究中找一個護身符貼在背後,這樣子慰藉自己:
「我研究的是地球上的人們與其世界與現象」
這樣一來我們就不會手足無惜的不知該如何是好,自設個框架會比較安全一點,就如前文Geertz說的,這些研究方法提供了我們界定問題的框架,整個 「地球 」就是我們研究方法的挶限性,離開了這裡,或許就要找更大、更好的解釋來說服自己安心的繼續做研究,同時也能說服他人…,但這也只是一種消極的說服理由,在有生之年中,登上了火星居住,發明了如史帝芬.金在小說中提到的 “跳特”,能在眼一開一合間跳越數百光年後的另一人類殖民地,我們還能繼續矇著眼,摸著一面為我們提供安全感的那 “框限之牆”,在這裡安心的說服自己繼續往前探索嗎?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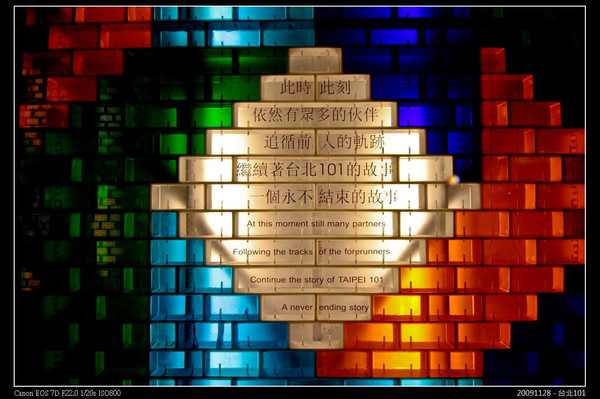
![[聊攝影340] Nikon Z 相機通用教學 Vol03. 主插槽選擇 [聊攝影340] Nikon Z 相機通用教學 Vol03. 主插槽選擇](https://i2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2/20240218204319_0.jpg?quality=90&zoom=2&ssl=1&resize=350%2C233)
![[攝影旅行團] 冰島白色歐羅拉11日之旅 [攝影旅行團] 冰島白色歐羅拉11日之旅](https://i0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5/20230510193108_14.jpg?quality=90&zoom=2&ssl=1&resize=350%2C233)


![[冰島] Dynjandi 丁堅地瀑布,冰島西峽灣最壯觀瀑布 [冰島] Dynjandi 丁堅地瀑布,冰島西峽灣最壯觀瀑布](https://i2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4/20240404153951_0.jpg?quality=90&zoom=2&ssl=1&resize=350%2C233)
![[冰島] Plane Wreck 飛機殘駭,空安意外下的獨特風景(附2024巴士時間) [冰島] Plane Wreck 飛機殘駭,空安意外下的獨特風景(附2024巴士時間)](https://i2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4/20240404165551_0.jpg?quality=90&zoom=2&ssl=1&resize=350%2C233)

![[台北課程報名] 打開你的攝影觀 – 構圖與攝影藝術 [台北課程報名] 打開你的攝影觀 – 構圖與攝影藝術](https://i0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20822161536_87.jpeg?quality=90&zoom=2&ssl=1&resize=350%2C233)
![[冰島] Rauðasandur 紅沙灘,冰島西峽灣獨一無二的存在美景 [冰島] Rauðasandur 紅沙灘,冰島西峽灣獨一無二的存在美景](https://i1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4/20240404160956_0.jpg?quality=90&zoom=2&ssl=1&resize=350%2C233)
![[冰島] Plane Wreck 飛機殘駭,空安意外下的獨特風景(附2024巴士時間)](https://i0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4/20240404165551_0.jpg?resize=1200%2C628)
![[冰島] Rauðasandur 紅沙灘,冰島西峽灣獨一無二的存在美景](https://i2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4/20240404160956_0.jpg?resize=1200%2C628)
![[冰島] Dynjandi 丁堅地瀑布,冰島西峽灣最壯觀瀑布](https://i0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4/20240404153951_0.jpg?resize=1200%2C628)
![[聊攝影340] Nikon Z 相機通用教學 Vol03. 主插槽選擇](https://i2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2/20240218204319_0.jpg?resize=1232%2C650)
![[攝影旅行團] 冰島白色歐羅拉11日之旅](https://i0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5/20230510193108_14.jpg?resize=1232%2C650)
![[台北課程報名] 打開你的攝影觀 – 構圖與攝影藝術](https://i2.wp.com/hojenje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20822161536_87.jpeg?resize=1232%2C650)

